【暢享絲路 遇見敦煌——第六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
為敦煌學走向世界構筑高地
——訪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
敦煌,承載著世界的目光。
敦煌學,從20世紀初發軔至今,一直牽動著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的心,並為之不懈奮斗,最終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境遇一步步走向今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喜人局面。近日,記者專訪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一同走進敦煌學發展的百年歷史長廊。
記者:敦煌學作為國際顯學,其起源是怎樣的?
趙聲良:眾所周知,敦煌學的起源與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密切相關。藏經洞位於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第16窟積沙時,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洞內出土了公元5世紀至11世紀初的宗教經卷、社會文書、中國四部書、非漢文文獻以及絹畫和刺繡文物等共計6萬余件。
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很快被往來於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的探險家獲悉。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奧登堡等英、法、日、俄等國的“掠奪者”接踵而至,相繼攫取大量文物,后流散於英、法、日、俄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吸引了西方許多漢學、藏學、東方學等領域的學者競相研究,特別是法、英、俄、日等國產生了一批在國際學術界有影響力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使敦煌學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
可以說,藏經洞的發現,是人類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推動了東西方學者的競相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形成了一門新興學問——敦煌學。
記者:敦煌學主要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麼?隨著時代發展,有何變化?
趙聲良:敦煌學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敦煌藏經洞文獻和敦煌石窟藝術。隨著時代發展,敦煌學研究范圍不斷延伸擴展,涉及宗教、藝術、歷史、地理、經濟、語言文學、民族、民俗等眾多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屬於交叉學科,其中也包括粟特文、回鶻文、吐火羅文等“絕學”“冷門”領域。又繼續擴展延伸至對絲綢之路歷史,中國西部古代民族文化以及中亞、西亞及南亞古代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研究,可以說敦煌學研究內涵豐富,包羅萬象。
記者: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到“敦煌學回歸中國”,幾代敦煌學人如何賡續接力?敦煌學傳承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趙聲良:由於20世紀上半葉復雜的社會因素,我國的敦煌學研究發展比較緩慢,學者和成果較少,國際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這極大地刺傷著中國學者的自尊心。
讓敦煌學回到中國是幾代學者的夢想。但藏經洞文物流散於世界多國收藏機構,這給中國學者的研究帶來極大困難和不便。20世紀初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的陳寅恪,是第一個看到國外敦煌資料的中國學者。他開創了敦煌學研究的風氣,也是最早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第一次提出“敦煌學”這個學科概念的學者。他還號召學者使用好遺留的敦煌文書,做好敦煌學基礎研究。
1935年至1938年,向達在歐洲調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書期間,抄寫了數百萬字的敦煌文書,為后來國內敦煌學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是我國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學的專門機構,在常書鴻的帶領下,開始臨摹工作,為開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領域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任所長。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段文杰、史葦湘、李其瓊、霍熙亮等前輩臨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經典的代表性壁畫,在國內外舉辦展覽,在弘揚敦煌藝術的同時,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對敦煌石窟藝術和圖像的關注和研究。
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初,接替常書鴻擔任所長,還是1984年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面對我國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學研究現狀都焦慮不安。他呼吁:要抓緊時間,急起直追,多出成果,才能趕上國際學術界前進的步伐。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擴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領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現狀,為國爭光!
段文杰率先垂范,夜以繼日,先后寫出《早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藝術》《晚期的莫高窟藝術》等論文,概括出了一部相對完整的敦煌石窟藝術發展史。在他的帶領下,經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員共同努力,除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外,還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等一系列出版物,敦煌研究院也從過去以敦煌藝術臨摹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石窟圖像、敦煌文獻、歷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領域的研究,產生了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這個科研團隊也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好評。
這一時期,還有不少人為敦煌學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值得一提——
1982年,敦煌研究院創辦了國內最早的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研究》,從不定期,到季刊,再到雙月刊,研究范圍不斷擴大,至今已出版200期,成為國際敦煌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專業核心期刊。
1983年,季羨林擔任會長的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相關高校、科研院所奮起直追,廣泛深入開展敦煌學各領域的研究,以豐碩成果為敦煌學當代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國社科院等相繼成立敦煌學研究機構,開設敦煌學相關課程,培養專業人才隊伍,保証了我國敦煌學研究事業后繼有人。
1984年至1998年,季羨林率領敦煌學界編寫了《敦煌學大辭典》,對總結國際敦煌學的研究成果並向大眾普及敦煌學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近40年的努力,我國在敦煌學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學者,貢獻了數以千計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敦煌學領域居於先進和領先地位,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
1988年8月20日,季羨林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一致贊賞。中國學者已不再耿耿於懷“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而是以開闊胸懷,歡迎全世界學者攜手從事敦煌學的研究。
記者:現在,國際學術界已公認中國是敦煌學研究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圍繞敦煌學研究,敦煌研究院有哪些主要成果?
趙聲良:敦煌研究院基於敦煌石窟及其藏經洞文物的多元價值,開展了石窟藝術、石窟考古、敦煌文獻、歷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領域深度研究,創立了以“客觀臨摹、整理臨摹、復原臨摹”為核心的壁畫臨摹方法,開創了多學科交叉的石窟考古報告編撰新范式,構建了敦煌石窟、敦煌藝術、敦煌文獻並重的學術研究體系。特別是近4年來,成果豐碩。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承擔和開展“敦煌河西石窟多語言壁題考古資料搶救性調查整理與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完成《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第二卷)編撰,推動《麥積山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第二卷和《炳靈寺石窟第169窟考古報告》《北石窟寺第165窟考古報告》編寫,開展《敦煌石窟內容總錄》修訂,出版《麥積山石窟內容總錄》﹔通過現代科技應用和多學科合作,探索的石窟寺考古理論、方法和技術,初步構建起石窟寺科學考古研究體系,形成了考古報告規范化編撰體系。
——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承擔“敦煌文獻釋錄與圖文互証研究”“敦煌中外關系史料的整理研究”“敦煌多元文化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國家級省部級及以上科研課題項目50余項﹔開展“海內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書信文獻整理與翻譯”“法藏敦煌漢文非佛經吐蕃文獻整理與研究”“敦煌研究院藏回鶻文文獻整理與研究”“吐蕃時期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出版了31卷大型圖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刊布了甘肅省13家單位收藏約6700件的敦煌藏文文獻﹔出版相關研究專著40余部,發表論文300余篇。
——在敦煌藝術研究方面,整理出版了敦煌藝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敦煌藝術大辭典》,全面展示敦煌藝術的整體面貌和研究成果,填補了敦煌藝術研究在大型綜合類辭書出版領域的空白,榮獲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開展“敦煌石窟盛唐壁畫色彩美學研究”“敦煌石窟供養人服飾研究及活化利用”“敦煌石窟樂舞文化研究”等國家級省部級藝術研究項目﹔圓滿完成國家版本館7個專題特藏室主視覺壁畫繪制任務,受到肯定與好評﹔持續創作蘊含敦煌藝術價值、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創作的大型壁畫《絲路文明》《絲路印記-玄奘西行》《錦繡絲路》等入選全國美展。
記者: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設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高地。那麼,我們是如何定義“高地”的,“高地”有哪些標准?未來,“高地”建設的規劃是怎樣的,又將如何實踐?
趙聲良:建設“高地”就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引領敦煌學研究,或者說吸引國內外學者到敦煌來,到敦煌研究院來﹔敦煌研究院也要搭建平台,團結、凝聚全世界敦煌學學者攜手敦煌學研究﹔高質量辦好《敦煌研究》《石窟與土遺址保護研究》兩個期刊,吸引全世界敦煌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傳遞敦煌學研究的最強音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敦煌研究院已發展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實體,今后將繼續秉承“開門辦院、開放研究”的宗旨,團結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學者,共同推動敦煌學研究,形成完善的石窟文化價值研究譜系,引領國際敦煌學研究方向,建成敦煌學權威陣地。一方面,繼續舉辦國際國內學術會議,邀請各國專家學者到敦煌交流、研討、講學,共同引領世界敦煌學的發展。同時,積極“走出去”,通過考察、交流、展示,讓敦煌學研究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繼續推動《敦煌研究》高質量發展,使其成為世界敦煌學最高水平、最新研究成果的權威展示平台。同時,加大培養力度,讓年輕一代成長為敦煌學界的中堅力量,讓敦煌學研究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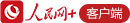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