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风从敦煌来
金城,阳光明媚,时光静好。
在自己的工作室,秦川完全沉浸其中,浑然忘我。连着几天,他一直在对四集纪录片《敦煌,千年不散的筵席》央视播出版的字音校对和画面进行修改。
“羊肚筋膜丰富,临出炉的刹那,浇上一股醋,趁热咬上一口,酸爽滑嫩的快感直冲头顶……”光看着诱人的画面,听着诱人的解说,就让人忍不住一个劲地咽口水,秦川自己也时时被美味“诱惑”,笑着坦承:“剪着,剪着,就饿了。”
秦川,我省著名纪录片导演。此前,他刚刚从新疆拍摄《石窟中国》回来。
“甘肃的石窟群,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基本拍了个遍。而《石窟中国》将展现中国石窟全貌,刚好让我‘补’全‘石窟课’,令我特别兴奋和期待。”从2004年起,自称“敦煌土著”的秦川从敦煌出发、守着敦煌拍了十几年,先后拍了15部、60多集纪录片,最终的成片总时长“两天两夜不吃不喝才能看完。”
风,从敦煌来,不眠不休。
(一)
1965年1月,秦川在敦煌莫高镇出生。
莫高镇离莫高窟很近,幼年的秦川就时常沐浴在“敦煌风”中,乐此不疲。莫高窟每年雷打不动的四月八庙会,在秦川记忆里“比过年还热闹”。
这一日,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不等天亮便拖家带口,带上吃喝,赶着马车、驴车,赶往莫高窟。其时,敦煌城里万人空巷,前往莫高窟的路上,则如记载:“车马喧闹,游人络绎。或轻裘缓带簇雕鞍,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板,高歌紫陌村头。”
一派热闹繁盛景象。
小时候的秦川,最喜欢在四月八跟着家人去莫高窟,“钻各种洞子。”那时候,莫高窟的洞窟还没有门。
其时,秦川对敦煌懵懂无知。莫高窟就像当时当地的时代广场一样,只图个热闹好玩。
后来当了记者,秦川一年跑几十趟莫高窟,可写来写去,来来回回“敦,大也;煌,盛也。”秦川不干了,莫高窟的博大精深,敦煌老百姓说不上就说不上,可作为媒体人,实在说不过去。
(二)
秦川想找到“敦煌文化的源头”,他向台里提出拍摄纪录片《大河西流》的建议。
思路,他都想好了。
那是2004年,酒泉电视台当时的条件并不好,不仅设备中低档,也没有专业的摄影师、剪辑师、灯光师,所以,秦川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都说:“这个人太可笑了,想出名想疯了。”
可秦川执拗。他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在敦煌整整跑了3年,很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从无人涉足的地方。
“8集片子投资不到10万元。对于大团队来讲,几乎等于没有投资。”这是秦川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印象格外深,时隔近20年,拍摄过程依然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采访车是临时借来的,现场拾音的话筒挑杆是一根自制木棒,每天野外工作十几个小时,最长的一天昼夜奋战22个小时,凉水、干饼就黄瓜就是可口的午餐;拍摄时间要么利用节假日,要么平日里加班一点点“攒”出来,没有补助、没有加班费,可“有梦想啊”,干得贼起劲。
随着拍摄的一点点推进,秦川惊喜地发现:疏勒河不仅连通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把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产生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疏勒河,就是‘敦煌文化的源头’,敦煌的母亲河啊。”
2005年5月,包含《敦煌的母亲河》《中国长城的尽头》《脱水的城堡》《西出阳关》《寻找玉门关》《三危佛光》《飞天情缘》《拯救敦煌》8集的纪录片《大河西流》终于“呱呱坠地”,在酒泉电视台首播,随后又在敦煌市开了一场观影会,赢得“一片叫好声”,一举“扭转乾坤”。
2006年12月,《大河西流》在《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疏勒河连同秦川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
第二年,《大河西流》为酒泉摘取了第一个国家级电视节目大奖——2005-2006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优秀电视专题片提名奖。
《大河西流》坚定了秦川的信心,也让秦川为自己定下不成文的“规矩”:凡拍纪录片,从立项开始,就得是央视标准,全国水平。
(三)
秦川创作生命的转折点,交汇于纪录片《大河西流》。
拍摄《大河西流》的时候,秦川采访了正在西部探险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镰。《大河西流》播映时,杨镰和同事纷纷热议。杨镰“纠正”大家“这可不是央视拍的,是酒泉台拍的”的时候,同事们直呼“不可能”。
可杨镰知道,杨镰相信。他找到秦川,直接授权秦川以自己的著作《黑戈壁》为剧本,拍摄同名纪录片。
曾经叱咤大西北黑戈壁的“黑喇嘛”丹毕加参,一度让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老百姓视为洪水猛兽。20世纪初叶,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牵动着整个亚洲的神经。但时隔多年,能找到的也仅有一段碉堡战壕,还涉及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该如何“复活”这段历史呢?
翻越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穿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此后两年时间里,秦川带领摄制组拍摄了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大量历史遗迹,采访了十余位草原牧民、人文学者,生动再现了20世纪初中亚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黑喇嘛”传奇。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紧张激烈的脉络冲突、变幻莫测的片子结局……2008年12月,《黑戈壁·黑喇嘛》在《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2008年11月,《黑戈壁·黑喇嘛》一举摘得“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的“十佳纪录片奖”。第二年4月,又受邀赴卡塔尔多哈参加“第五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展映单元。
这是秦川第一次走出国门,亮相国际纪录片节。
(四)
“今年,也不能挂‘空挡’啊。”
这句话,像“闹铃”,适时响起。
一部接一部登上央视,一部接一部获奖,秦川,正在兴头上,特别是,“敦煌就像个宝库,随时打开都有新题材。”
2009年,秦川要拍《敦煌书法》。
他知道,在敦煌的艺术宝库中,除了壁画彩塑,还有一枝光芒四射、瑰丽多姿的艺术奇葩——敦煌书法。
敦煌,是中国书法的重要发源地。敦煌书法范围甚广,从藏经洞出土的书写本到古遗址出土的汉简、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碣,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多姿,行草隶篆皆备,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敦煌,有大量汉代到宋代的书法真迹,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汉字第一次脱离识读功能而成为独立的抽象艺术——草书,也发生在敦煌……关于“敦煌书法”,可以说的话、讲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秦川“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四集《敦煌书法》七个月的拍摄,让秦川“特别过瘾”, “情景再现”的表现方式,仿若时空穿越,让他与古代书法家亲密地“朝夕相处”起来:
——东汉,张芝敦煌家中后院。正在挥毫泼墨的张芝,看到家人将绢帛送去染房染色,突发奇想,若在白绢上写字,如何?
其时,纸张刚刚发明出来,还比较粗糙,尺幅不大,价格不菲,书家很少用。而西汉就已经产生的章草,也“只能像豆子一样,一个一个‘蹦’出来,是无法‘连体’的。”
铺开绢帛,蘸墨提笔,张芝行云流水般一口气写下去,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因为绢尺幅大,且细腻、吸水性极好。”
就这样,草书诞生了。那一刻,汉字从认读工具,真正成为一门石破天惊的书法艺术;那一刻,一颗巨星在中国敦煌闪耀登场,又整整影响后世1800多年。
——敦煌汉简发现之前,人们不知道汉代人写的毛笔字是什么样的。只能通过漫漶不清的石刻,通过刀法看笔法,“可笔锋下的轻重缓急,是雕刻家的,不是书法家的。”
……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201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评选结果,《敦煌书法》喜获“优秀国产纪录片中篇奖”。
(五)
2013年,受甘肃省委宣传部委托,秦川又开始创作拍摄6集大型纪录片《敦煌画派》。
这一次,秦川拍了整整三年。三年中,秦川长途跋涉数万里,搜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线索,终于将敦煌画派纷繁复杂的碎片一一厘清,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美术画卷。
“这三年,非常痛苦,简直痛不欲生。”秦川的言语神情中,透着化不开的痛,尽管这只是回忆。
秦川、安秋两位导演花了整整五六个月的时间,整理学术资料,最终形成26万字的学术本和分集大纲。
“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艺术价值,还要有观赏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秦川他们跑了七八个省,在画面呈现上也是绞尽脑汁,颇费心思。
拍“敦煌画派”,常书鸿、张大千、于右任、段文杰、董希文、吴作人、关山月、常沙娜、李其琼、万庚育、史苇湘、欧阳琳、孙纪元、何鄂……绕不开的闪耀之星,名单很长很长。
可该怎么呈现呢?
纪录片《敦煌画派》一开场,张大千这位21世纪全世界公认的画家率先登场,“张大千的权威性、影响力不容置疑,他都拜倒在敦煌壁画面前了,那么敦煌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的地位也就毋庸置疑了。”秦川想借“大千”之力,让观众一下子就对敦煌有一种仰之弥高的印象。
事实证明,秦川“赌赢了”。
时隔8年,拍摄万庚育的一幕幕场景,犹在秦川眼前。
2013年5月10日那一天,当时已92岁高龄的敦煌美术家万庚育老人郑重地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方丝帕,又小心翼翼地展开——徐悲鸿、廖静文、吴作人、李苦禅、董希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20多位美术大家的签名,竟密密麻麻汇集在这方小小的丝帕上。
作为徐悲鸿的弟子,万庚育并非寻常人,她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半个世纪都在敦煌,看惯了大漠长天,孤泉冷月,黄沙絮絮,却在漫天黄沙即将把数百个灿烂夺目的洞窟掩埋和毁灭之际,用满腔热血挽救敦煌,保护敦煌,研究敦煌。
万庚育喜结连理的日子,徐悲鸿带着师生前来祝贺,就用毛笔在这方丝帕上一一签下名字。自此,这方丝帕成了万庚育最珍贵的宝贝。文革时,又害怕,就拿水洗,竟洗不掉。
真是万幸啊,手绢皱皱巴巴了,可签名依然清晰。拍摄时,万庚育因脑梗已基本失去语言能力,日常交流全靠子女翻译。可当导演安秋问她:“您这一辈子,跑到敦煌,受了那么多苦,后悔不后悔?”时,老人突然说话了:“不……后……悔……”
“为什么不后悔呢?”
“艺术……艺术……艺术……”老人重复了好几遍,令人动容。
……
2016年1月18日,在兰州万达影城举办的首映式上,纪录片《敦煌画派》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
“秦川,这是不是你拍得最好的片子?”首映式后,有人问。
“不敢说最好,但这是我拍得最难的片子。”秦川实话实说。
(六)
2018年2月的一天,秦川正骑着自行车在酒泉的大街上溜达,突然接了个电话,电话内容是让他接拍一部叫《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敦煌首次跨出国门,与其他国家做一次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
秦川心里清楚,自己对吴哥窟一无所知。但他相信,敦煌可以和任何一种文明对话,“把敦煌吃透了,再去对话,找共同点,找不同点,就不难。”
此后,秦川、安秋两位导演开始“恶补”吴哥窟。其时,有关吴哥窟的书并不多,但痴迷吴哥窟、每年要去好几回吴哥窟的台湾著名作家蒋勋,写了不少吴哥窟的书,《吴哥之美》便是其中经典。
身未动,心已远。不断“恶补”之下,秦川对吴哥窟心向往之,也发现了莫高窟、吴哥窟的诸多异同——
莫高窟、吴哥窟的重新发现,乃至被推向世界,竟然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人参与其中。此人名为伯希和。
巧,还巧在:后来,法国人把吴哥窟的石雕,偷运到法国巴黎;其时,藏经洞亦被发现,伯希和组建考察队来到敦煌,用相当于法国市面上一件文物的价值,拿了7000多件敦煌宝贝,也偷运至法国巴黎。
100多年前,两大古迹,遭同一批人以同样方式的“发现”;并且,两大文明在同一家博物馆、同一间展厅展出,这家博物馆正是法国吉美博物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物,有这样奇妙的机缘。”秦川已经感到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那喷薄欲出的巨大冲击力。
“太美了,太震撼了!” 秦川第一次到吴哥窟,就被巨型石雕所构筑的空间艺术震撼了。他舍不得放过任何一块石头,“吴哥窟的雕塑太细腻了,就像拿着针在石头上绣花。”
“艺术之美是不需要翻译的。”镜头里,吴哥窟的精美雕塑一一呈现;脑海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一一映出,举着摄像头,秦川突然“顿悟”,语言不同、民族肤色不同,美的艺术可以让人心连通起来,“这不就是‘一带一路’讲的‘民心相通’吗?”
没错,没错,“民心相通”,最佳的打通方式就是艺术,“‘一带一路’建设,就应通过文化进行更多沟通。”
2019年8月31日15时,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盛大首映,成为“一会一节”闭幕式上的最大亮点。
其实,播映之前,有人担心两集100分钟太长,特别是怕不少嘉宾年龄大,坐不住,建议只播一集。
可秦川犟,别人说什么都不听,坚持两集全播。结果,全场1200多名嘉宾安安静静看完,剧终,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二年,入选第八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优秀长片奖、荣获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优”作品、中宣部2020年度优秀地方外宣品二等奖……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先后摘得4项全国大奖,还在河北衡水剧院,捧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26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纪录片提名奖。
从莫高窟前仰望星空,到衡水湖畔摘下“星光”;从黑戈壁到红地毯,秦川走了整整20年。
他走得步履铿锵,别人“恨”他,“秦川,你太不厚道了。收那么少的钱,这不是破坏行情吗?”
“真的是情怀。”秦川笑笑,自嘲对自己确实挺“刻薄的”,拍了15部纪录片,做导演没导演费、写稿子没稿费、摄像没摄像费、剪辑没剪辑费,没钱咋办?就“拿肉夯呗”,透支休息时间、透支身体……
(七)
很多人知道,秦川拍了《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很多人不知道,在拍《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的同时,他还接了纪录片《中国石窟走廊》的拍摄。
两个都是大片,还要同时交稿,只有一年时间,秦川心里暗自叫苦,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
“太狠了。对自己太狠了。”秦川知道,这就相当于头上顶着两个大罐子,还要快速奔跑,还不能让罐子掉下来,2018年、2019年,拍这两部片子的时候,秦川过着“非人”的生活。
好在,两部片子都是石窟,有交叉、有穿插。
好在,两部片子都让秦川兴奋。
甘肃,最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便是绵延三千里的石窟走廊。不仅最古老的石窟在甘肃,甘肃石窟营造延续时间也是最长的,长达1600多年,而且,千年营造从未中断过。秦川趁机将甘肃境内石窟群的历史脉络、文化价值,全部梳理出来了。
莫高窟代表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代表了最优秀的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国的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以及记忆的细节,都保存在敦煌,要唤醒民族记忆,敦煌就是最好的“开关”……
“敦煌,是文化和艺术的汪洋大海。有着穷其一生也做不完的文章。20年,我只是舀了敦煌的一瓢水而已。”说起敦煌,秦川兴奋起来,滔滔不绝。
风,从敦煌来。只有起点,从无终点……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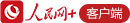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